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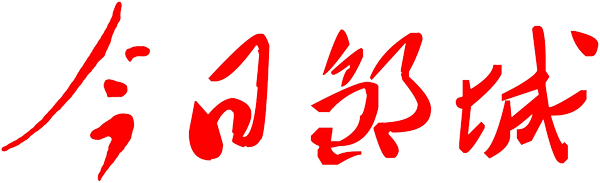
月是故乡明
李传云
又是一年中秋至。
傍晚时分,我站在城市高楼的阳台上,看那轮渐圆的月亮淡淡地挂在天际,却被霓虹灯的光芒衬得有些苍白。忽然就怀念起乡间的月来——那清澈如水、亲近可人的月,偶尔有轻云飘过,月亮周围便泛起彩虹般的光晕,真正的“彩云遮月”。
记忆里的中秋,总是与丰收的忙碌和喜悦交织在一起。金秋九月,绿中透黄的庄稼在阳光下颜色清晰得刺眼。农人们戴着草帽,在田野里忙着秋收,刨花生、掰玉米,割豆子、刨红薯。待到日头西沉,乡间的夜晚以炊烟袅袅宣告夜幕的降临。家家户户的屋顶上,白色炊烟在明媚的月光下升腾,在空中弥漫散开。
中秋的夜晚,是属于团圆的。灯火次第亮起,全家人围坐在饭桌旁,那时尽管物质匮乏,但桌上依然摆放着白菜粉条炖猪肉、家养的小公鸡,还有豆角、黄瓜、豆芽儿等时令蔬菜。最难忘的是母亲总会特意做一道糖醋鱼,说是寓意“年年有余”。
中秋也是乡村的“美食节”,在平常是难得吃到的美味。
吃过晚饭,家家都把月饼拿出来敬月亮而后品尝。每家都是那种老式月饼,厚厚的、圆圆的、黄澄澄的浸润着油彩。掰开来,绿色的、红色的甜丝,黄色花生瓣儿,无色的冰糖都露了出来,让人馋涎欲滴。
在我的故乡,还有一种独特的习俗——制作芝麻糖火烧。中秋午后,家庭主妇们便开始忙碌。醒发好的面揉完后切成面团,用擀面杖轧成圆饼,放入研成细末的红糖作馅包起来,再拍上芝麻。平底锅热后,掌握好火候,很快就烙出两面金黄的饹馇。厚厚的熟芝麻夹杂着焦糖,又香又甜的味道在小院里弥漫,洋溢着节日的气氛。刚出锅的火烧外酥里嫩,咬一口,红糖汁顺着嘴角流下,那香甜的滋味,至今仍萦绕在记忆深处。
月光下,孩子们总有属于自己的乐趣。包餐后溜出家,呼朋引伴,背着大人悄悄地潜伏到谁家的瓜田、菜地里去了。
以往听大人们说,八月十五的晚上,端一盆清水放在菜地里的豆角架或辣椒架下,耳朵贴在水面上,侧耳倾听,准能听到月宫里嫦娥和玉兔的悄悄话。在儿童们的世界里,充满了对这个美好传说的向往。
记得有一年中秋,我们几个小伙伴真的端了盆水,趴在菜地里听了半天,虽然什么也没听到,但那份期待与想象带来的快乐,至今想来仍觉温馨。
月亮渐渐升高,蓝白相间的天空比平时更显得高远。村里庄外吃过晚饭的人们,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。“相见无杂言,但说桑麻长”,大家围坐在院子或街头巷尾,各自品评着谁家的庄稼长势好。老人们则会说起往年的收成,念叨着“八月十五云遮月,正月十五雪打灯”这样的农谚。
凉风习习,伴着蟋蟀、蛐蛐等秋虫愉悦地欢叫声,白雾淡淡的朦胧,每一片庄稼的叶子都被露水打湿,显得油绿青翠欲滴。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犬吠,更添几分乡村夜晚的宁静。
如今,在城市里,中秋节几乎都是在忙忙碌碌中度过,全然没有了往昔节日的气氛。超市里琳琅满目的月饼摆满货架,包装越来越精致,却再也找不到儿时那老式月饼的醇香。城市里的月光,总是被高楼切割得支离破碎,被霓虹冲淡了本色。
或许,只有在乡野田间,人们才感觉真正体会到中秋节本来的内涵。毕竟,在这个从中国农耕文明孕育而来的佳节,只有将收获、庄稼、月光、田野、秋风、虫鸣等交融,才能唤醒那穿透千百年的恒久意义。
月到中秋分外明,今夜的月亮,是一面古老的铜镜,映照出尘世的沧桑。在团圆的渴望里,它高悬着,沉默着。而我的思绪,却如一匹脱缰的马,在中秋的夜晚,奔涌在故乡的小道上。
“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”。夜深沉,月儿更明,故乡的亲人,无不思念那些长期漂泊远在他乡的游子。在这斑斓的秋色中,惟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。
或许,正是因为有了这份对故乡的眷恋,有了这份对团圆的期盼,中秋的月光才会如此动人,如此令人魂牵梦萦。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