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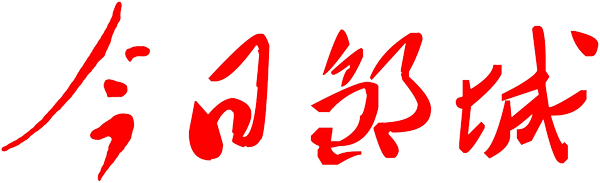
古人中秋雅趣
王玉美
中秋的月色,是淌过千年时光的清浅溪流,漫过朱楼画栋,漫过寻常巷陌,也漫进古人案头、杯中与眉间。彼时无霓虹闪烁,唯有一轮明月悬于天际,古人便以案上焚香、登楼望月、煮茶品饼、酌桂花酒、月下赏桂等雅事,将佳节过成了一首温润的诗,每一笔都浸着对时节的珍视,对生活的热爱。
案上焚香是古人中秋的开篇雅韵。《东京梦华录》载,宋代中秋夜“贵家结饰台榭,民间争占酒楼玩月”,无论朱门还是陋巷,案头总会燃一炉香。或取沉香切片,或用桂花合香,青烟袅袅间,香气与月色交融,清冽又温柔。女子会对着香雾缭绕的月轮默默许愿,盼“貌似嫦娥,颜如舜华”;男子则借香抒怀,愿“胸有丘壑,志存高远”。香燃过半,月色已从檐角爬至窗棂,案上的香灰积成细浅的小山,恰似把中秋的时光轻轻拢在案头,静谧又虔诚。此时风过庭中,携来远处的虫鸣,便引人想起高处的月色该更清亮——索性拾级登楼,让月光裹着清风漫过衣襟。
登楼望月时,古人总爱让目光随月色漫向远方。唐代李白在中秋夜登谢朓楼,写下“长安一片月,万户捣衣声”,月光洒在楼檐瓦当,也洒在他举杯的指尖,仿佛能触到千里外的乡关;宋代李清照与赵明诚曾登青州城楼,“云中谁寄锦书来?雁字回时,月满西楼”,月色漫过栏杆,把对远方的思念拉得绵长。寻常人家也爱寻一处高阁,孩童趴在栏杆上数云间星子,老人摇着蒲扇讲嫦娥奔月的故事,偶有晚风拂过,带起檐角铜铃轻响,与月下笑语叠在一起。若恰逢邻里同登一楼,还会互赠自制的酥糖,你尝我的芝麻味,我品你的花生香,月色下的寒暄,比糖更甜。待夜色渐深,指尖触到微凉的风,便知楼头月色虽好,不如归院煮一壶热茶——案上的茶器早已备好,就等月光一同入席。
归院坐下,煮茶品饼是中秋最熨帖的闲逸。明代文徵明在《中秋》诗中写“煮茶烧竹待明月”,他爱用虎丘泉煮雨前龙井,茶烟袅袅间,茶汤泛着浅绿的光晕,与窗外月色相映。月饼是酥皮的,咬开时碎渣落在案上,内馅或豆沙或枣泥,甜而不腻。家人围坐案前,一人一盏茶、一块饼,茶的清苦解了饼的甜糯,饼的绵密衬了茶的清香。月色透过窗棂落在茶盏里,漾起细碎银辉,连时光都慢下来。待茶过三巡,舌尖还留着茶香,案头那坛桂花酒又引人侧目——中秋的夜,该让酒香混着桂香再添几分暖意。
酌桂花酒时,古人总爱与月色对饮。《武林旧事》记南宋中秋“禁中赏月,有赏月延桂排当”,宫人将新酿的桂花酒斟入银杯,酒色浅黄,开盖便闻见桂香。文人雅士则在庭院中设席,举杯邀月,“桂子月中落,天香云外飘”,酒液入喉,先是桂花的清甜,而后是酒香的醇厚,暖了脾胃,也醉了心神。偶有桂花瓣落在酒杯里,随酒液轻轻晃动,恰似把月中桂树摘了一瓣放进杯中。酒至微醺,目光落在庭中那株桂树上——月光正给花枝镀上银霜,此时不赏桂,更待何时?
月下赏桂是中秋的收尾雅事,也最见古人的细腻。唐代白居易在洛阳宅中种桂,中秋夜“满院桂花闲不扫”,他拄着拐杖在桂树下踱步,月光透过枝叶洒下,地上花影斑驳如绣,连呼吸都裹着桂香;宋代杨万里见桂花开得繁盛,写下“不是人间种,移从月里来”,伸手轻折一枝,桂香便沾了满袖。古人赏桂不贪多,只取一两枝插在瓷瓶里,置于案头,让桂香伴着月色,连梦都是甜的。
如今,中秋的过法虽添了许多新意,但古人案头的香、楼头的月、杯中的茶与酒、庭中的桂,仍在时光里散发着温润的光。每当中秋月色升起,仿佛还能看见千年前的古人,在香雾中许愿,在高楼上眺望,在茶饼间笑语,在酒香中沉醉,在桂树下流连。那些雅事,早已不是简单的习俗,而是藏在中华文化里的温柔,让每一个中秋夜,都满是诗意与暖意。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