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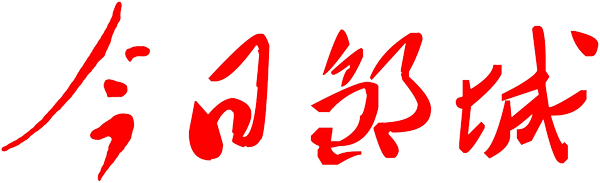
客从何处来
青柠
天地有节,人生有时。
“大寒时处三四九,天寒地冻冰上走”,大寒节气,离春节只有十天了。
早上散步的时候,抬头看见下弦月挂在体育馆银边上一竿高的地方,月色皎洁,一定照得到那些游子的行囊,一定照得到他们归家的路。天南地北,离家的人纷纷切换回家模式,“回家”的念头,一笔一划反复在心头镌刻。回家过年,这是一个不需要任何理由的决定。牵挂始终萦绕在心头,家的温暖在遥遥招手,多少个日夜的奔忙只为欢聚的那一刻,家人围坐,灯火可亲。
作为365天中最重要的日子,年是一场盛大的仪典,凝结着思念的期盼、团圆的渴望;是一次庄重的集会,慎终追远迎福纳祥;是一回身心的洗礼,给人安慰与放松,归零和重启。
大寒至立春,人们除旧布新、制作腊味、祭灶……在寒冷的日子里忙得火热。年味就在这一饮一食、一仪一典、一言一语之间。
不经寒夜与风雪,又怎么会如此在意故园灯火?深深佩服先人的智慧,于一年中最寒冷的时节里设立这个重大的节日。无论怎样难熬的时刻都已过去,在对春天的期盼里满血复活,所有一切都来得及,都可以从长计议。
我也要回老家去,给爷爷奶奶上坟。一抔黄土,衰草苍苍。寒凉的风声呜咽,四处的青山高远。点香的火燃着了附近的枯草,火苗蹿得很快,烤得我脸庞发红发热。坟地离村子二里地,临水而居的人们总喜欢把家安在靠近水源的地方,日出而作,日入而息。忙碌了一辈子的爷爷奶奶葬在山坡高处,远远地眺望曾经的老屋石墙,守护着那片播撒过汗水的田野,守护着儿孙们又一轮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奔忙。
回老家总喜欢四处转转,儿子说我是在“回味童年”。门前的小溪早已没有了小时候的清澈,接近干涸的水边也会走过几只大白鹅,歪歪斜斜。儿时的菜园种满萝卜白菜大葱,绿意盎然。如今无人照料,只剩下密集的杨树在疯长。方正高大的新居盖起来,很气派也很舒适,显得本身低矮的祖屋更加局促。那么多年过去了,爷爷一手建造的祖屋依然牢固安全,筑墙的土是爷爷从五里外的魏石沟用小车推来的,涂上之后,墙面细腻光滑,唤作“姥娘土”。院子空旷,以前栽植的槐树、苦楝、桑树都已不见踪影。院墙东边的花椒树还坚守着锋芒,肩并肩站成祖屋的一道围墙。老井还在,四季长青,滋养了我,还有我的亲人。在这冬天的阳光下,点点热气升腾。用井绳打水,左一拽,右一拽,就能打个满桶。“像你这么大的时候,我就能挑水了”,说给儿子听,他似信非信。肩膀头是练出来的,我不仅能挑水,还会换肩,虽然那水桶几乎擦着地。爷爷说,我在村里也会是一个“好把式”,爷爷还为我划了“大屋窖”后面的一块地,准备给我盖屋娶媳妇。
“某时某人某地”云云,跟儿子说起我童年往事,希望他能了解。一一应答,态度蛮好,但不曾在这里生活过,我看未必能走心能记得。
与老家的连接让人心安,老家的安静无与伦比,没有一丝喧嚣,静如世外桃源,无限接近幸福。
那些贪玩的孩童,风一样走过,嬉笑打闹,无忧无虑的,似我的当年。我不认得他们,他们也不认得我。我成了老家的新客了。虽然我端起碗就喝家乡的水,虽然我拿起煎饼卷上大葱就吃得很香甜,虽然我尽力用纯正的乡音亲切地打着招呼,但我接不了地气了,我是乡亲眼中的“异客”了。生活需要缝缝补补,重回故里,我一路的苦衷又能说给谁来听呢?
家是远行的起点,也是归程的终点。路遥马急,来自五湖四海,从踏上归途那一刻,我们就是回家的人。尽管“儿童相见不相识,笑问客从何处来?”
前不久,在同事履新的欢送会上,大海同志引用了高适的诗:“莫愁前路无知己,天下何人不识君”,我以为是最好的送别词。“老马识途”“等闲识得东风面”“新妇识马声,蹑履相逢迎”“不合时宜,惟有朝云能识我”……人海茫茫,一个“识”字何其珍贵。
一年又一年,年是一代又一代的传承。
乙巳年春节,是春节申遗成功后的第一个春节,也是儿子留学回来以后的第一个春节,好好过,当下都要好好过,都要“巳巳如意”。
因为,每一个此刻,又将是明日的念想。

